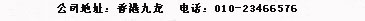普洱的茶山
春风拂满三月,总会想起普洱大大小小的茶山,想念那里的美好,思念那里的友人。今年计划清明节去趟普洱,可重庆到普洱的直航最近取消了,只能取道版纳或澜沧,算来算去感觉路上花的时间太长,在三天假期往返行程太匆匆,只好割舍了这个计划。元旦想去一趟,没有成行,三八节想去一趟,没有成行,清明节想去一趟,结果还是没有成行。什么时候可以来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呢?
一、世界茶源
普洱被誉为“世界茶源”,据说有五大证据:一是茶树始祖,在景谷发现万年前的宽叶木兰化石;二是茶树远祖,在普洱多地发现万年前的中华木兰化石;三是野生茶树,在镇沅千家寨发现年野生茶树王;四是过渡型茶树,在澜沧邦崴发现年过渡型千年古茶树;五是栽培型茶树,在景迈山保存完好的千年万亩栽培型古茶园。因此,世界茶叶委员会于年授予云南普洱“世界茶源”称号。
普洱茶特指云南大叶种乔木茶,是一种独特的种质资源,分布于云南的普洱、西双版纳、临沧等区域。由于这一地理区域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特别是气候、土壤、生物、地质、地形和茶树品种的综合影响,形成了普洱茶的独特风格,其它地区即使引种云南大叶种种植,但茶的品质根本无法同云南普洱茶相提并论。同时,普洱茶基本上都是分布在至米的高海拔地带,不仅水土纯净,植被丰富,生态环境极好,而且远离外来污染,还有大量的益虫益鸟,这既有利于茶树的生长又不容易发生病虫害。许嘉璐先生在年写过一篇题为“美好的普洱”的短文,他这样盛赞普洱:“我把普洱茶视作珍品,而他们却从小到老与之为伴,畅饮一生。我喝不够回味无穷的浓香的普洱茶,茶如人生,人生如茶,先苦后甜,叶片离开茶树之后,生命犹在,年愈久而味愈浓,让我每一品咂,就和大自然贴近了一步。而他们则祖祖辈辈享乐其中,时时感念着天地之赐、先民之恩。”他一方面是对普洱茶文化的称赞,另一方面也是对普洱生态文明的赞叹。
普洱茶通常以山头命名,出自哪个山头的茶叶通常就以这个山头的名字命名普洱茶。普洱茶非常众多,市场上很难判别。不过,高品质的普洱茶通常是选择树龄超过百年的古茶树头春鲜叶,全程纯手工制作而成。正宗的古茶树都是被野放的天然茶树,茶林即森林,茶树在荒山野岭慢慢生长,不打农药,不用化肥,自然生长百年甚至千年。古树茶条索粗壮肥厚,耐泡度很高。而台地茶则是整体茶叶条形细小,耐泡度要弱得多。去普洱之前,不仅很少接触普洱茶,对于台地茶和古树茶也都没有丝毫的概念。但离开普洱,不仅知道了古树茶和台地茶的明显差异,而且对于古树茶却有着独特的感知。
二、普洱茶山
普洱有很多的茶山,据说有8座茶山是最为著名的。不同茶山的普洱茶,不仅茶的品质有一定的差异,而且茶的口感也各不相同。一般情况下,清明前后的普洱茶是最好的,所以每到这个时候都会有世界各地的普洱茶喜好者从四面八方聚集到普洱的各个茶山,就为了能够在这个最好的季节亲临其境感受普洱茶原生的天赐神韵。
在普洱见到的第一座茶山是营盘山。营盘山在普洱市城区东南郊,大约半小时左右的车程。因为路途不算远,而且这里可以感受到非常壮观的无边际普洱茶园,所以我刚到普洱的第二天,他们就特意带我去营盘山实地感受壮观的普洱茶园。营盘山的茶园是台地茶,依山而上,一层一层的茶山,绵延起伏,一眼望去,满眼都是重重叠叠的普洱茶山,非常震撼。据说营盘山茶园是云南省内最大的连片万亩生态有机茶园,有2.4万亩台地普洱茶,已建成为集茶叶科学研究、环境保护、生态农业以及观光旅游、休闲度假为一体的“中华普洱茶博览苑”。后来去过好几次营盘山,最喜欢在茶园里悠闲散步,聆听茶花细语,不经意间生发出对茶园崇敬的感叹。
由于曾经分管景迈山申遗的缘故,加上多次陪同考察,前前后后估计去过20多次景迈山,因而对景迈山不仅最为熟悉而且蕴藏着最深的情感。景迈古茶山距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茶叶面积达2.8万亩,其中古茶园就有1.64万亩,是目前世界上保存最完好、年代最久远、面积最大的人工栽培型古茶园,被誉为“茶树自然博物馆”和“古茶活化石园”。景迈山古茶园文化景观正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虽然去过很多次景迈山,但百去不厌,每次去景迈山都有不一样的感知。
困鹿山在宁洱,离普洱城区较近,先后2次现场考察和3次陪同考察,加上普洱茶集团郑总的多次介绍和对普洱茶集团的实地调研,因而对困鹿山也算是比较熟悉,而且特别的喜欢。困鹿山古茶园在清代曾是清宫贡茶的指定生产地,因而称“困鹿山皇家古茶园”,在古茶园里转上一圈感悟古茶树的独特魅力,在路边简陋的小屋泡上一杯古树茶,能够真切地品味出“皇家茶园”的独特风韵。困鹿山古茶树群落,总面积1万亩,属半栽培型茶树群落与阔叶林混生形成的原始森林。虽然“皇家古茶园”目前只有多棵古茶树,但困鹿山的茶叶却有很多种,而且茶的品质都还比较好。
无量山主要在景东,是离普洱城区相对比较远,而且当时的道路不是很好走,路上耽误的时间往往比较多。我曾3次去景东,每次去都比较匆忙,因而可以说只是略知一二,不过对于景东无量山以及无量山云雾中神秘的普洱茶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景东,我们看到了最原生态特别粗壮的普洱茶树。景东的无量山是世界茶树的发源地之一,被誉为茶起源的摇篮和普洱茶的古老故乡。景东野生茶树分布面积28.6万亩,其中无量山居群23.5万亩,哀牢山居群5.1万亩。栽培古茶园3.71万亩。由于这里是高纬度与高海拔,气温低、雨量较少,因而这里的普洱茶通常香气较沉、带微苦、微酸。
茶树起源于第三纪宽叶木兰,景谷是唯一发现茶树起源始祖宽叶木兰化石的地方,至今约万年,历史非常悠久,因而景谷被称为“茶祖之乡”。目前栽培百年以上古茶园差不多有3万多亩,野生茶群落面积6万多亩。景谷的苦竹山离县城10多公里,海拔米,是著名古普洱茶的原产地之一。我曾5次进出景谷,有一次特意专程到农户家调研,了解古茶树的科学保护与合理利用,还同他们一起兴奋地品味他们自做的古树茶。
邦崴在澜沧县富东乡邦崴村,我的扶贫联系点是澜沧县富东乡富东村,富东村与邦崴村毗邻,每次去富东村都会顺道去邦崴村看看那棵千年的古茶树,或许是景仰亦或是膜拜,在古茶树周边走上一周,抬头看看依然青春而繁茂的古茶树,油然而生几分敬意。据说邦崴村发现的千年过渡型古茶树彻底改变了茶叶原产地的传统学说,甚至改写了人类种茶的历史。邦崴茶,叶质厚,内质饱满,口感刺激性强而集中,香型层次明显。我每次去富东村的扶贫点,都会生出一些联想,为什么人们很喜欢邦崴村的邦崴茶,茶叶价格也比较昂贵,但就在近邻的景东村,同样是古树茶,但价格却完全是两个模样。如果富东村的古树茶能够比肩邦崴村,富东村不就成为富裕村了吗?
说起普洱的古茶树,一定会提起镇沅县的千家寨,很多人不远万里慕名来到这里,就想目睹这棵拥有年历史的野生茶王树。我曾经3次去镇沅调研,但很遗憾没有去千家寨。千家寨位于普洱市东北部的镇沅县九甲乡和平村,分布在哀牢山自然保护区的原始森林中,海拔至米左右。千家寨野生古茶树群落是全世界目前发现的面积最大、最原始、最完整的以茶树为优势树种的植物群落。在千家寨上万亩野生茶树群落的环抱中,有一棵古老的普洱茶树,树龄达年,是至今发现的世界上最大最古老的普洱茶野生茶树,这就是举世瞩目的世界野生茶树王。
在普洱,还有一些茶山,我虽然没有去过但还是偶尔听人说起。比如,江城县的牛洛河自然保护区有12.8万亩的现代茶园。西盟县的佛殿山有野生古茶树群落,自古就是普洱府的八大茶山之一。还有宁洱县的板山,是清代较早的贡茶产地。有一次原本约好了去板山普洱茶基地实地调研,但时间好像来不及就改道去了困鹿山的会连古茶园。不过,普洱大大小小的茶山,实在是太多太多,很难一一走到。但从已走过的茶山还是能够感受到普洱茶山的概貌,能够体会到普洱茶山独特的美丽和奇特的魅力。
三、普洱茶韵
普洱茶的好坏,通常取决于五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原料,原料是根基;二是生产,工艺是核心;三是存储,良储是保障;四是醒养,醒养是要道;五是冲泡,冲泡是关键。所以,判别一款好茶,始于原料而终于冲泡,品质是基础,冲泡是赋予普洱第二次生命的过程。
再好的普洱茶,如果存放不好,也是枉然。真可谓买茶容易放茶难。所以,良好的存储是普洱茶特别重要的保障。如果是紧压的茶饼,不用拆开包装,如果是散茶,最好存放在紫砂或紫陶罐中。关键是要有一个“干燥、通风、无异味”的环境,也就是要保持环境干净、无异味、保持通风和稳定的温度和湿度。很多人喜欢把茶存在冰箱里或放在柜子中,其实这是不科学的,普洱茶存放在冰箱里面会阻止普洱茶的生长,存放在柜子里会因为不通风而发霉。当然,普洱茶最好也不要存放在卧室,普洱茶也最怕化妆品。
普洱茶看似简单,但却非常复杂。我们通常看到的一款普洱茶,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聚合体,是一个复杂多样、充满活力而又富于变化的生命体。比如,茶原料的茶树年龄不一样,所处的地理环境不同,海拔高度不同,仓储的时间和空间也不尽相同,此外,这个生命体还会因为时间和环境的不同而不断发生变化,从而带来甚至是完全不一样的口感或感受。同一款茶,由于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不同的泡茶人,却呈现出不一样的神韵。普洱茶通常可以分为生茶和熟茶两大类,无论是生茶还是熟茶,都存在原料的产区与海拔、山头与村寨、古树与台地、树龄长与短、采摘与季节、纯料与拼配、仓储年份与地点等一系列复杂的因素,这些复杂的因素纵向与横向相互交织,使普洱茶变得深不可测,气象万千。
普洱茶的冲泡受茶具、水温和时间的影响,因此,很难用一个标准的动作或技术冲泡每一款普洱茶,所谓不同的人泡出不同的普洱茶,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泡出不一样的普洱茶。即便能泡得出一款好生茶但不一定能泡得好熟茶,泡得好新茶但不一定能泡得好老茶。泡好一泡普洱茶,必须先了解茶的茶性,在冲泡的过程中能把这款茶的茶性充分激发出来,因此,即使是非常资深的茶艺师,对于自己不是很了解的某款普洱茶,泡起来往往都很难做到淡定自若,甚至偶尔也会茫然不知所措。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转载请注明:http://www.puershizx.com/pesjj/7809.html
- 没有推荐文章
- 没有热点文章